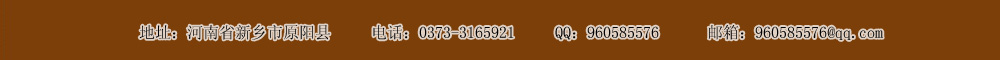这部纪录片揭开中国崛起迅速发展背后的黑
故事发生在一个有着30多年废旧塑料加工历史的沿海小镇。
这里没有阳光海滩、比基尼俊男美女,
这里只有成千上万,堆成了一座座山的垃圾。
在这里,
有些村子十几年前地下水已不能饮用,
如今都是用塑料桶买水喝。
回收塑料的村民整日泡在浓烟里,
说自己决定不查身体了。
在垃圾堆里长大的小孩们,
有臭哄哄的垃圾堆就能玩得不亦乐乎:
小男孩翻到一支废弃的针管,
这便成了他珍贵的玩具,
拿着针管往嘴里吸水,
“有水了!有水了!”
他边说边又把这支医疗垃圾塞进嘴里。
和他一起的小伙伴,
也挖出一些脏兮兮的,
不知做过什么的塑胶手套。
他们把手套吹成气球,
高高兴兴玩了一天。
来自世界各地的塑料垃圾构筑了影片主人公依姐童年生活的“王国”。
12岁的依姐早在4年前就应该入学,
那时她的父亲承诺等打工赚了钱就送她上学。
一晃4年过去了,依姐仍然在不断地做着抗争。
这些垃圾来自
美国、西欧、日本、韩国等地,
飘洋过海,
进入中国海关,
源源不断地输送到
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广东等省份,
被废旧塑料回收工厂买走,
用于生产再生塑料。
这是导演王久良
继年
以北京被多座垃圾场包围、
河流和地下水污染严重
的严峻现实为背景
制作《垃圾围城》后,
进阶级的作品
--纪录片《塑料中国》。
短短26分钟的片子,
却在豆瓣上评到9.2的高分,还一举拿下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的大奖,
但是没有人能为此高兴起来。
里面拍下来的每帧每个画面,都像是在狠狠撕开中国发展背后的痂,露出底下血淋淋的鲜肉。如果没有年的那次美国之旅,王久良可能还跟其他人一样被蒙在鼓里。那次,他跟着一个合作伙伴来到了加州的垃圾回收站,
图为美国加州某垃圾分拣中心。这里的垃圾在经过简单分类之后,玻璃和金属就近回收处理。
满心期待能看到一套不一样的处理系统,
但却只看到成吨的垃圾堆积成山。
流水线上的工人熟练地分拣垃圾,
除了一些容易分解的,
大量难以分解的塑料垃圾,
都被打包送往一个地方。
采访某垃圾回收公司经理时,
对方指着一辆绿色的集装箱卡车说,
“看,那就是运到你们中国去的!”
车上装的正是刚刚工人们挑出来的塑料品。
经理称公司收回来的垃圾经过粗分,
出口到别的国家
“为什么要送去中国?难道中国回收塑料垃圾的技术会比美国好?”
经理摇头否定:
因为中国市场最好,
愿意出其他国家的两倍价格。
王久良一直在想,
这些洋垃圾进入中国后,
最后去了哪里?
对环境、人体健康会不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做一部塑料垃圾纪录片的想法由此而生。
躲过村支书,逃过警察,受过不明人士的追打,制作过程历时六年,十分波折。
六年后,王久良剪出一个26分钟的媒体版。
在这个版本里,
脏臭的废弃塑料堆积在村庄的各个角落,
国家明令禁止进口的医疗废物是孩子们童年为数不多的“玩具”
脸色蜡黄的妈妈,
在垃圾堆旁喂奶。
小婴儿的脸上,
爬满了苍蝇。
小姑娘在污水池旁,
蘸着脏水洗头发。
这里有上千家大大小小的回收坊
回忆起作坊里的气味时,
王久良皱眉摇头,
“非常臭。”
他说。
这里经验丰富的工人,
拿打火机来烧一烧,
闻闻味道就能分辨垃圾的种类。
“聚氯。”
老工人淡淡的回答。
他觉得它不好闻,
却不知道里面含有剧毒。
塑料造粒是他们日常的工作。
将塑料放在铁管里,
螺旋加热融化塑料,
经过滤网后,
相对纯净的塑料就被压面条似地挤出去,
过水冷却成型变硬。
当地人传说,
塑料造粒最多干三年,
不然生育能力就丧失了。
而片中主人公之一的作坊老板,
从二十岁到三十岁,
干了十年。
这些塑料胶粒,
不久后运往沿海的工厂,制成玩具,出口海外。塑料垃圾来中国转一轮,除了浪费了清水、空气和土地,没有任何用处。
那些以此为生的居民也是迷茫。捡一斤布赚一毛钱,夫妻两人一起干,一个月顶多赚块,但换回来的却是越来越糟糕的身体。一个老人蹲在台阶上抹眼泪,“我身上的这癌啊,不知道能活到什么时候了。”旁边的老人插话说,“现在的癌症奇怪了。年级小的也得。”
片子中的老板,腰上长瘤子,经常头痛,疑为早期心脑血管症状。医院,不肯。怕查出毛病要花钱。
“他媳妇和我说,破碎塑料一小时,整个嗓子咳着疼。”王久良说,“片子中没有表现出来,她的腿和脚都挠烂了,因为脏东西,过敏。”
拍摄半年后,王久良的眉心长出氯痤疮,这是因为长期接触氯元素。他发现很多人都长这个,拍过一个小孩,满头满脑包括脖子后面,长满了氯痤疮。
垃圾遍地的工厂,浓烈的塑料烟气,不洁净的环境让这名工人的孩子皮肤受到了严重的病菌侵袭(黄水疮)
“山,山不好了,
水,水不好了,
说句难听的,
只有钱好了。”
王久良曾经向村里的老人打听“谁家得了病”,但老人听了的第一反应却是跟他列举,哪家哪家的人还没有得病。
其实,这个村庄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个农村的缩影。很多人不知道,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的多亿美元的货物中,竟然有超过11.1%都是这些亟待回收的垃圾。这些垃圾流向了多少地方,搞不清楚。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报告显示,年全世界电子工业将产生0万吨电子垃圾,其中72%进入中国。而且大多数会走进小乡镇,成为村民的唯一生活来源。
原来,
中国不仅仅是世界工厂,
还是世界的垃圾场。
片子里的一个场景让人特别难忘记,拍摄快要结束的那几天,王久良遇到了一个开着红色卡车的大哥,他的车上载着废弃塑料,准备扔到路边。
大哥下车看到王久良手里的相机,没什么反应,只是一边干着他的活一边说出这么一番话:
“拍照?你拍个照片有什么用?拍个照能解决问题?国家真要是取缔的话,可以从源头上抓嘛。那么像这些塑料垃圾,日本、美国、西欧,它们是怎么过来的?我就想问问它们是怎么过来的,怎么进到我们中华民族共和国领土上的?”
说完,他转身离去,下一次回来的时候,身后或许又是一车子残废品。
导演王久良说,他不再满足于只呈现一个现象,而是想讲人的生活。本片主人公有两位,一位是文中的作坊老板,一位是开头提到的12岁的依姐。
“片子中埋了一些隐喻,比如老板的价值观,他想买辆车,干各种脏活,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这是没问题的。但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悖论。他挣钱的目标,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事实上,他在追求更好生活的过程中,已经失去了更好的生活。”
很多时候,你不得不惊讶于当今社会的分裂。一方面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已经执行国际一流的工厂排放标准。另一方面,在农村,仍延续着最原始落后的工业生产方式。像纪录片中的土作坊,华北平原有很多,小皮革、塑料、化工、酸洗厂等等,就在田间地头盖一栋砖房,支两架旧机器,有污水就直接在地里挖个坑排了,渗下去,天长日久,掩埋好,上面继续种庄稼。
主人公依姐在拍摄期间是9-11岁,家贫上不了学,只能在家帮父母带着4个弟妹,以及熟练地分拣塑料。她想上学,但压抑着不说出来。她告诉王久良,再等几年,自己就可以去打工了,挣钱供弟弟们念书。
依姐抱着刚出生的小妹妹
故事的最后,依姐终于能够上学了。但王久良又说,“他们那边结婚特别早。16岁就结婚了。”总之,依姐很可能辍学。假若继续拍摄依姐,那很可能又是一个新的故事——一个16岁的小女孩如何去了东莞、深圳的工厂,去打工。
而老板也实现了他的心愿,带家人来北京天安门看升旗,他在车里教导四岁的儿子,要努力学习,才可以在北京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来源综合:
腾讯新闻、
恒地移民专业办理美国、澳大利亚、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塞浦路斯、新加坡等各国移民投资项目及护照办理,欢迎来电咨询!
服务
厦门:方洋
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