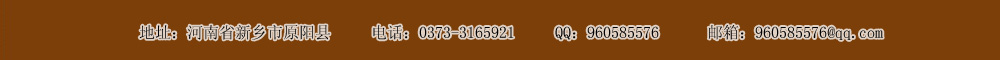叶志东教授谈载药支架在支架内再狭窄的探索
专家简介——叶志东教授
医院心脏血管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生导师,第一届国际血管联盟中国分会青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血管联盟中国分会血透通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血管外科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腔内血管学专业委员会腔静脉梗阻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颈动脉专家委员会、血管通路专家委员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分会心胸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医师协会血液透析通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师协会血管外科专科医师分会常务理事等。AVS杂志审稿专家,《中华血管外科杂志》等核心期刊编委,中华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
01
精彩演讲
《下肢动脉治疗理念和技术变革》
目前全球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PAD)发病率为3~10%,70岁以上患者发病率为15~20%。一项全球性荟萃分析显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高发病之一。据估计,全球约有2亿的人群罹患此病,而且该数字仍在逐年上升。因此下肢动脉硬化疾病的治疗亟需引起重视,PAD的治疗手段也从药物治疗、开放手术、腔内微创到综合治疗历经四大阶段。
最早是通过外科手术对症治疗,即“哪里病变切哪里”,这一简单直接的理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最大的问题在于并非所有下肢病变部位都能暴露,尤其对于靠近内收肌管,以及胫前、腓总动脉深部的病变。因此搭桥成为了解决这一难点的不二之选,从早期的股-股转流、股-股搭桥,膝上膝下以及踝部病变,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手术效果虽好,也有其难以解决的问题:第一,手术要在全麻下进行,绝大部分高龄/合并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难以耐受;一项旨在评估股腘动脉旁路手术并发症发病率的研究显示,术后30天并发症发病率高达37%,包括伤口感染、出血等,这对于高龄/合并有较多基础疾病的患者而言可能是致命的。
因此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迎来腔内介入时代。腔内技术的应用带来了下肢病变治疗的革新。原来开展膝下搭桥治疗5年通畅率仅为50%左右,而通过球囊扩张等腔内技术则能显著提高远期通畅率。BASIL研究旨在评估搭桥术(BSX)与球囊血管成形术(BAP)治疗重度下肢缺血的疗效对比。结果显示术后3年内两组远期通畅率与二次干预率无显著差异,但术后5年时,BAP结果明显优于BSX,这一研究奠定了腔内介入治疗在下肢血管病变中的治疗地位。
同时疾病的分型也有了改变,年,TASC合作组修订并颁布了第二版指南(TASCII),相较于第一版,TASCII的制订将原有首选开放手术的TypeC级逐渐调整为首选腔内介入的A级和B级。相信随着经验的积累及器材的不断更新,外周血管疾病将会首选腔内治疗。
欧洲ESVS最新指南推荐,外科手术适用于无手术高风险的PAD患者,病变长度25mm,自体静脉可以用于搭桥,预期寿命2年的患者。而病变<25mm,则首选腔内介入。该指南肯定了腔内治疗在整个下肢疾病治疗的重要地位。
上世纪90年代国内治疗PAD首选PTA+BMS,相较于单纯PTA,可以有效避免弹性回缩。但后期发现,下肢动脉不同于其他外周血管,如肾动脉、颈动脉、锁骨下动脉等位置相对固定,其支架扭动对于内皮损伤较小。而股腘动脉在运动过程中,由于其所受力学的特殊性,往往需要应对压迫、屈伸、弯曲以及扭曲等挑战。
因此支架在股腘动脉内面临着更大的断裂变形风险。支架断裂会引起早期的再狭窄,通常术后1-2月出现再闭塞的情况,往往与弹性回缩,支架内断裂引起急性血栓形成有一定关系。后期主要是由于支架本身对内膜的刺激导致内膜增生,引起支架内再狭窄(ISR),因此在应用PTA+BMS的同时,血管外科医生对ISR及其发病机理也愈加重视。
一方面,从肢体锻炼角度,支架重叠处容易互相扭转,支架越长,钙化越严重,越容易断裂;另一方面,支架的径向支撑力会持续刺激内膜增生,尤其早期为了获得更大管腔,会选择与管腔1:1或更大比例的支架植入。但与此同时,oversize的BMS会对血管内皮造成持续的损伤,导致过度的内膜增生。因此支架理念的变革也由此悄然而生。临床开始通过减少支架的应用,选择直径较小的支架(降低COF)来减少支架对血管壁的刺激。
同时应运而生的还有药涂球囊(DCB)。但对于长段、严重钙化病变,应用DCB后的补救支架植入率明显增加。
为了更好地应用DCB,减少夹层的出现,临床引入了血管准备的理念,如今这一理念已成为整个下肢腔内治疗的标准步骤。无论是应用DCB还是药物支架,都应进行充分的血管准备。
目前血管准备主要是通过球囊扩张方式的改进(如逐级扩张、长时间扩张)、球囊性能的改进(刻痕球囊、高压球囊等)以及减容装置的应用,包括血栓减容(如Angiojet)、斑块减容(如JetStream)等来减少夹层发生,优化管腔获得。但减容的同时依旧对内膜造成了损伤,因此单纯减容并不能获得满意疗效,需要结合DCB才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随着DCB在临床的广泛应用,其在一年内对于合适病例的一期通畅率可以达到89%甚至90%。但三年后,PTA+BMS的通畅率明显优于DCB,临床开始重新审视支架的作用。
DEBATE-SFA研究显示,相较于PTA+BMS组,DCB+BMS组12个月再狭窄发生率明显减少(17%vs47.3%,P=0.),免于TLR减少趋势。临床开始在DCB后常规应用BMS,但医疗费用较高,于是药物支架(DES)的出现带来了新的展望。
目前国内主要有两款药物支架,其中Eluvia由于其独特的PROMUS聚合物涂层技术能够持续一年进行药物缓释,覆盖再狭窄进程。同时通过IMPERIAL研究结果显示,Eluvia的一期通畅率高达91%,令人惊喜。
而DES的出现,相较于DCB,孰优孰劣呢?RealPTX研究将例入组病例随机分成DES和DCB组,平均病变长度mm,结果显示DCB组补救支架率达25.3%,病变越长,DES组的远期通畅率更优。且3年随访结果显示,DES比DCB作用更持久。但总体通畅率仍需进一步提升,所以支架性能还需不断研发探讨,如何将支架对人体内膜刺激的损害降到最低,这将是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最后,尽管目前腔内治疗已是大势所趋,但对于手术技术的需求不可偏废,依旧需要引起重视,尤其对于一些特殊病例,如短段或者骨质覆盖的病变,手术将是最后一道防线,手术技术也是血管外科的基石。
目前PAD患者逐年增加,治疗依旧是以腔内为主,手术为辅,同时需要秉承leavenothingbehind理念,尽量减少支架应用,但对于长段或者严重钙化病变以及支架内再狭窄的病变,药物支架依旧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充分的血管准备可以优化下肢疾病的治疗。而全新的DES由于其独特的聚合物技术能够利用最少的载药剂量达到最优的临床结果,希望未来可以获得中国患者应用DES的真实世界数据,为广大的中国患者带来更多获益。
02
专家专访
载药支架的出现,为外周血管介入治疗带来了哪些突破?引发了哪些争议?
自年7月17日,波科公司的Eluvia支架上市以来,为血管外科界带来了革新性的里程碑技术。回顾以往外周血管介入的治疗历程,从早期的开放手术到现在的介入治疗,包括介入的理念技术和器具都得到了极大提升,我个人认为这一路走来有三个里程碑式的突破:
第一个,传统开放手术迈入腔内介入治疗,使巨创走向微创。但普通球囊和普通支架在临床应用时存在一定问题,如弹性回缩、内膜增生导致支架内再狭窄,支架断裂等,于是在摸索中,我们迎来了下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
第二个,药物球囊(DCB)的应用。下肢血管不同于其他部位的血管,因为运动受力导致支架植入受到了极大挑战,容易对血管壁造成损伤,而DCB的应用则可以避免支架植入。但很快临床实践发现DCB存在很大局限性:一方面,早期应用DCB疗效满意,但随着时间延长,弹性回缩等问题的出现,极大降低了远期管腔通畅率;另一方面,DCB对于复杂、长段、钙化等病变,效果并不理想,需要植入补救支架的比率甚至达到一半以上。因此,在不断探索中,我们又看到了新的突破口。
第三个,载药支架(DES)的出现,实际上相当于将金属支架的支撑作用与药物的抑制内膜增生作用合二为一,我认为这是第三次技术性的革命。当然,载药支架上市后,也产生了很多争议,比如载药支架的应用是否会更新目前下肢腔内治疗的理念,是否会改变药物球囊或普通支架的治疗地位等诸多热点问题,大家都各抒己见,阐述不同观点。
因此,今天我就这方面的热点问题发表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和些许体会。更多的数据还是有待Eluvia上市后的真实世界的数据结果,才能获得更有力的循证医学支持。无论如何,我认为载药支架的出现会为下肢血管腔内治疗提供一个有力的武器,很多复杂病例也会因此得到极大获益,这是我个人观点。
载药支架的成败由支架主体,药物和药物释放机制3部分决定,在这其中,您认为哪一部分更为关键?
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载药支架顾名思义既有支架的成分,又有载药的成分,同时药物还有不同的释放方式,到底哪一个环节更为关键呢?我认为三个环节都关键。
第一,药物球囊的出现是因为普通支架存在定位不准,容易断裂,且刺激血管内皮造成内膜过度增生等问题,所以支架的性能非常重要。
第二,药物球囊出现后,载药剂量也颇为关键。年Katsanos教授一篇轰动性的文章提示:患者全因死亡率增加与紫杉醇的远期毒性有关的可能。到目前为止,尽管有很多循证医学证据证明载药剂量和死亡率不一定相关,但那篇文章依旧起到了警告和提示的作用,即过多的剂量可能会对病人带来不利的后果,所以出于对病人安全性的考虑,载药的成分和剂量也尤为关键。
第三,药物的释放方式。药物球囊是瞬间释放的机制,因此为了达到更多药物能够扩散至血管内皮下基层的目的,往往在设计时,会通过托载高剂量的紫杉醇来降低器具在输送期间,因为管壁摩擦以及血流冲击时所导致的的药物丢失。而高剂量的药物可能对病人的安全性会造成一定影响。所以如果能通过托载低剂量的药物,同时兼顾疗效,这种载药方式将有很大优势。
载药支架也有瞬间释放的机制,瞬间释放即指在前一个月内,药物抑制作用明显,但随着时间的延长,药物抑制作用会逐渐减弱,这与药物缓释机制完全不同。
药物缓释机制可以控制药物释放的剂量和时间:
①避免浪费;②避免因为药物释放过量,游离于体内造成的损伤;③可以长期有效地抑制内膜增生。所以我认为缓释放的涂药方式,是目前最先进的一个理念,它可以保证持久的远期管腔通畅率。综上所述,这三方面都很重要,不论是支架性能、药物成分和剂量,还是药物释放方式,缺一不可。
从概念上讲,在新生病变中使用载药器械是再狭窄的“一级预防”策略,而在再狭窄病变中使用器械(尤其是ISR)则相当于“二级预防”策略,那么目前临床DES在ISR病变中的治疗数据如何?
因为波科公司的Eluvia载药支架上市后,我们连续应用了三例患者都是支架内再狭窄(ISR),所以在此分享一些应用体会。
首先,只要支架植入就有支架内再狭窄的风险,原因之一就有支架本身的刺激作用导致的血管内皮过度增生,而载药支架的药物作用可以有效抑制内膜增生。
第二,支架内再狭窄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ISR有很多的治疗手段,最常见的是用不同的球囊进行扩张,比如普通球囊、切割球囊、高压球囊、双导丝球囊等等,和普通球囊相比,特殊球囊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更大。同时也有应用药物球囊或者采取减容技术进行扩张的手段,当然减容还属于OffLabel。
而今天谈论的是一个新生事物,即Eluvia载药支架。在临床遇到三例支架内再狭窄的患者,都是因为支架断裂造成的支架内再狭窄。支架一旦断裂,单纯的球囊扩张和减容都不合适,只能在支架内再接支架。而在药物支架问世之前,临床医生尽量避免植入支架,原因有二:
①支架内套支架,管腔会变细,同时可能会再出现断裂问题;
②再度植入支架,将重新刺激管壁导致内膜增生。
现在有了载药支架后,一方面,金属裸支架的支撑作用可以有效解决部分弹性回缩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药物作用可以有效抑制内膜增生,改善支架对血管壁的刺激,所以从机理出发,相较于其他治疗手段,载药支架治疗支架内再狭窄能有更好获益,这是理论上猜测。
希望最终在真实世界能得到这样一组数据来证明这个猜测。如果确实结果良好,我认为载药支架在支架内再狭窄治疗的适应证上可以扩大。
如何看待载药支架的出现对传统器械(如传统球囊扩张/金属裸支架植入)技术应用的影响?
在载药支架出现之前,临床医生对药物球囊的应用有一个倾向:即不论出于经济因素或者心理作用,应用药物球囊后都尽量避免支架植入,所以对于这类病人有时反而因为刻意避免金属裸支架的植入而造成更早期的闭塞,它主要的问题在于药物球囊无法解决弹性回缩的问题。
所以需要了解哪一类病人容易出现弹性回缩,进一步了解病变类型,往往严重钙化病变、长段病变、CTO病变以及合并有糖尿病足病变等类型,目前在国际血管外科界被公认为是极具挑战性的病例,挑战性的病例则意味着用传统方式,包括球囊扩张、金属裸支架植入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对于这类患者的治疗,我认为载药支架是有其绝对的独到之处。
载药支架的应用并不意味着药物球囊或者裸支架的淘汰。尤其对于短段、钙化并不严重的病变,药物球囊能够避免金属支架的植入,同时还为疾病二次干预植入支架提供了余地和空间。
同时金属裸支架也有它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一些特殊部位,比如腹股沟韧带区转弯处和腘动脉区P1、P2、P3段,依旧属于支架的相对禁放区。尽管目前有很多仿生支架可以跨到P1、P2、P3区,但总体而言效果较差,所以裸支架的研发要继续进行。单纯的Eluvia支架也不能替代其他特殊专门为胯关节设计的支架。所以从支架设计方面,金属裸支架依旧有它的应用空间。
所以于我而言,载药支架主要是对于复杂病变、长段病变、钙化病变以及有早期再狭窄风险这类病变的治疗,有它的独到之处。
03
病例报道
一、病例情况
性别:男
年龄:59
主诉:间歇性跛行2月余,跛行距离米,左侧较重,疼痛部位小腿后侧。患者年因左侧股动脉闭塞行股动脉支架置入术,2月前症状复发。
查体:双侧股动脉搏动弱,双侧腘动脉、胫后动脉搏动弱、足背动脉搏动未触及。ABI:右0.87;左0.75
既往病史:糖尿病30余年,规律应用利拉鲁肽1.2mgqd、甘精胰岛素20u、口服二甲双胍mgtid;冠心病5年余,年行冠脉支架置入术,无吸烟、饮酒史。
术前影像学资料:
术前影像学诊断结果: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左侧股动脉支架术后闭塞(Tosaka3型),右侧股动脉狭窄。
二、病例特点
中年男性,既往存在吸烟等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既往左侧股浅动脉支架植入史,间歇性跛行症状典型,疼痛位置提示病变部位在股动脉;CTA证实左侧股动脉支架术后闭塞(Tosaka3型),支架断裂?
三、治疗方案及制定策略
1.拟先行右侧股动脉入路,翻山至左侧尝试开通;
2.如顺行通过失败则尝试逆穿腘动脉P2或P3段,尝试逆行开通;
3.通过病变,预扩后如无明显弹性回缩及限流性夹层,可使用药物球囊,否则需要置入普通支架或者药物支架。
四、拟用手术器械及药物使用
术前及术后阿司匹林mgqd,硫酸氢氯吡格雷75mgqd;
穿刺针、普通血管鞘、90cm长鞘,cmMP导管、导丝、普通球囊、药物球囊、普通支架、药物支架
五、手术过程
1.病人摆位:平卧位
2.入路选择:右股动脉
3.术前造影:
4.术中特别要求(抗凝、肝素化等)
穿刺成功后经鞘管注入普通肝素IU
5.手术过程:
患者入手术室后,平卧位,常规消毒铺巾,应用1%利多卡因行右侧腹股沟浸润。麻醉后,采用SELDINGER技术行右侧股动脉穿刺,留置血管鞘,注入肝素IU,应用翻山技术将长鞘置于左侧股总动脉后行血管造影,见股浅动脉中远段闭塞,支架断裂,远端腘动脉P1段显影,在CXI及VER引导下使用V18导丝、T12导丝通过闭塞段血管并将导丝远端置于真腔内,应用SABER(3-mm)、Mustang(5-mm)行股浅动脉、腘动脉序贯扩张后,见腘动脉存在限流性夹层,遂置入Innova支架(5-mm)及Eluvia支架(6-mm),近端使用药物球囊(微创)扩张,再次造影见股腘动脉管腔通畅,血流速度满意,支架形态及位置满意,术闭拔除鞘管,使用Exoseal封堵右侧股动脉穿刺点,压迫10分钟,加压包扎,返回病房。
6.术后造影
六、随访需求及医嘱
术后右下肢制动4小时,给予阿司匹林mg,qd;硫酸氢氯吡格雷75mg,qd;低分子肝素IU,qd;三月后门诊复查
七、手术总结
患者左侧股浅动脉支架术后12年余,再发间歇性跛行症状2月余,CTA证实左侧股动脉支架术后闭塞(Tosaka3型),支架断裂,术前造影示左侧股浅动脉及支架闭塞,闭塞长度约20cm,该例患者闭塞起始部存在一较大侧枝,通过时有一定难度,另外支架断裂处内膜增生较重,通过相对困难,我们使用长鞘+VER导管+支撑导管增加支撑力,使用T12导丝通过病变,球囊扩张后支架断裂处残余狭窄较重,我们置入了一枚6-mmEluvia药物支架;另外腘动脉存在限流性夹层,因此置入一枚5-mmInnova支架
往期推荐
空中百家讲坛
叶志东:最新指南对VTE防治的进一步优化
「智行E时代-非凡实例」医院下肢学术沙龙
血管资讯器械百科专区
网址:xgzx.talkmed.